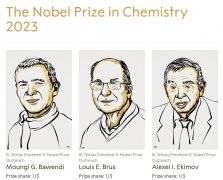天辰app从脱亚到入亚,黄皮肤给日本人带来了怎
已有人阅读此文 - -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0年来,针对这一标志性事件,史学家和战略研究者从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等角度做出了无数分析。
在日本历史学者真嶋亚有的著作《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中,作者另辟蹊径地从种族角度审视了这一事件。她拈出日本海军中佐藤田菊一12月8日的一段日记:“记住了吗?美国。三十余年积怨之刃即将斩向你的胸口”,并指出,这“三十余年的积怨”包含自1919年巴黎和会及其后华盛顿、伦敦裁军会议以来日本受英美打压而产生的人种对立情绪。在当时,这种对立情绪或隐或显地支配了从上到下的所有日本人,天辰app更成为军国主义操纵民众的灵丹。
那么,这种对立情绪是如何形成、累积、爆发的呢?在书中,真嶋亚有回溯了明治时代以来日本所经历的人种体验。跟着作者的视角,读者或许可以看清日本近代以来时而“脱亚”、时而“入亚”,乃至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等行径背后的种族逻辑。
“西化”背后,人种问题浮出水面
鸦片战争后,天辰app日本眼看中华帝国的衰退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为避免重蹈大清的覆辙,决定走上开国维新的道路。从此,原本在中华文明辐射下的日本,开始远离中国、否定亚洲,这种脱亚意识成为推动日本走向西化和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日本为了使自己作为‘日本’继续存在,选择了西化”,试图用“文明开化”来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真嶋亚有认为,当日本人选择西化的同时,出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非西方的日本无法通过西化具体实现自我界定;‘人种’这一宿命般的差异最为明确地分割了西方与日本”。也就是说,“西化”不仅没有使欧美在根本上承认与接纳日本,反而更加凸显了日本与西方国家人种上的异质性和与东洋人种的同质性。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一跃跻身列强行列,民族自信心大增。但是“日俄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成为西方萌发人种厌恶、人种排斥等的心理契机”。由于在东亚日益扩张壮大的日本与在亚洲寻求“门户开放”的美国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美国出现了大规模排日运动,日本政府则对美国的排日运动表现出强烈抵制。罗斯福评价道:“日本人自尊心强烈、敏感、好斗,而且他们还沉浸在日俄战争胜利的喜悦中,因此绝不能掉以轻心。”后来,美日达成了“绅士协定”,日本承诺主动限制国民移民美国,这对当时的日本政府和精英阶层来说是一种屈辱。
虽然跻身列强俱乐部,但作为唯一的非西方国家,日本既无法在国力上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也无法跨越人种的壁垒得到西方世界的尊重与认可。这种局面,使日本的精英阶层产生了非常微妙的自卑感。1908年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中这样描写:“(三四郎旁边的男子)说:‘洋人就是长得好看!’三四郎没说什么,只是应了一声,露出一抹微笑。于是,胡须男接着说,‘我们真可怜啊,脸长成这样,身体还这么弱,虽说日俄战争赢了,日本成了一等强国,可还是不行啊!’”
浮出水面的人种对立问题,为以“脱亚入欧”为国家方针的日本设置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为此,日本的精英阶层又提出了种种调和东西的论调。例如,大隈重信提出日本“东西文明融和之地”的观点。一面竭力避免日本与西方人种摩擦问题浮出水面,一面提出文明融和的概念,以使日本在东西之间找到稳定的定位,不再摇摆。他指出“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和代表者,有责任指导亚洲劣等文明国家,推动它们走向文明”。
历史现实是,这种在日本上层精英中流行一时的论调,十几年后便随着日本“人种平等提案”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以及1924年美国排日移民法案的通过而烟消云散了。
日本鹿鸣馆的西式舞会
日本鹿鸣馆的西式舞会
“坏孩子俱乐部”里的他者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日本跻身“一等强国”后首次参加的大规模国际会议。作为“五大强国”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国家,日本全权代表团在各种场合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蔑视。乔治·克里孟梭甚至对身边的法国外交部部长大声说,明明世上有“金发女人”,“我们却要在这里和丑陋的日本人面对面”。在此氛围下,巴黎和会召开后的第二个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发表演说,要求把废除种族歧视的条目添入《国际联盟盟约》。
作为文明国得到西方认可,是日本近代以来追求的最大目标。可是日俄战争前后,“黄色人种”这一身份正在成为可能动摇日本“文明国”定位及其认可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提交“人种平等”提案以自我防卫,其真正意图是使日本获得和西方对等的待遇。“人种平等”提案包含一种精神上的保证,力图使文明和人种坐标轴上摇摆不定的日本稳定下来并确保其“文明国”的地位。
最终,在英美的阻挠下,“人种平等提案”未能通过,作为补偿,日本获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虽然啃下一大块“肥肉”,但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人种平等提案”失败是近代日本在人种问题上的一大挫折,表明了名义上与英、美、法、意比肩的日本不过徒有虚名而已。石桥湛山毫不留情地嘲讽日本,“明明矮小体弱,偏偏还要加入坏孩子的团体,以欺侮他人为业”,于是“这个矮小体弱的孩子遭到了坏孩子团体的嘲弄”。
更令日本民众心态爆炸的是,1924年美国通过了“排日移民法”,将日裔移民定性为“不能归化的外国人”,对其采取全面禁止措施。法案引起日本举国上下的激昂反应,有报纸将法案实施的7月1日视为“国耻日”,因为“美国在日本人的额头上烙下了劣等人种的烙印”。
虽然有石桥湛山这样的知识分子站在批判角度指出,日本政府既没有提及自己对其他亚洲人的歧视待遇,也没有提及美国对其他亚洲人的歧视待遇,“只要日本人能享受到和白人同等的待遇,他们就满足了”,这种态度“利己、卑屈”,根本无法得到世界的尊敬。但这一事件确确实实让日本精英阶层认识到,无论如何西化,都会因无力改变肤色而无法得到归属感,这就给日本的国策从“脱亚入欧”转变为“脱欧入亚”提供了一个契机,并让日本就此走向“实力至上”的道路。
马基雅维利主义背后的人种阴影
在抛弃了文明融入、人种平等的理念转向“实力至上”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也转向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1930年代起开始在东亚大肆扩张,最终在1930年代末形成德意日三国轴心。
不过,正如驻美大使珍田舍巳说过的,种族偏见就好像“海德拉”(拥有不死之身的九头怪,被砍掉的头会长出来),只会根据不同情况反复显现或隐藏,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真嶋亚有敏锐地观察到,与对外关系的现实主义相应,日本在与列强的对比中认识到了自己“自然资源贫瘠”,进而在国内滋生出一种作为支柱的精神主义。真嶋亚有将其称为“基于现实主义的精神主义”,并揭示出这种精神主义也具有人种上的侧面。她指出,“日本虽然基于现实中的共同利害与德国、意大利结盟,但它在心情上也热切期待和白人结盟,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感。”
与此同时,作为头号种族主义者的纳粹德国和希特勒,对日本民族的态度可谓是根本不放在眼里。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日本极力掩盖纳粹德国对日本的种族歧视,还特意删除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中把日本视为二流民族的相关论述,但无法抹杀在德日本公民不断遭到歧视和骚扰的事实。1942年,希特勒还爆出了“当前的战争是决定生死的战争,重要的是取得胜利。为此,我们不惜与恶魔联手”的言论。德日同盟背后这种挥之不去的人种阴影,也导致德日高层一直没有达成互信。日本还构想过与德国种族主义背道而驰的犹太人自治区,称之为“河豚计划”。
纵观明治维新到战败前的历史,近代日本一直在文明与人种、东方与西方之间左右摇摆。在真嶋亚有看来,日本的精神构造是在欧化与国粹、崇美与排美、媚外与排外等两个极端的夹缝间不断摇摆形成的,处在不停的自我否定当中。
战败后,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崇拜美国的潮流,在某种意识上也可以算是“近代日本人种意识的‘总决算’”。作者写道:“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近代日本化为废墟,宣告终结。”可是,由近代人种体验而滋生的忧郁、寂寞与不安,却持续残留在日本国民心中。
《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在日本获得了极大成功,不到两年就出到了第三版,还得到各大报纸乃至西方媒体的推介。作为一部处女作,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除了本书内容具有话题性和公共性外,作者真嶋亚有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手法也功不可没:大量的个人案例,以及对回忆录、私人通信、游记、文学自传等材料的引用,一改学术著作的严肃面孔,让普通读者更容易接近;个人体验与群体视角的结合,更全景地展现了近代日本社会的人种认知。
最重要的是,作者为许多历史事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珍珠港事件,是日美人种问题积怨的爆发;又如日美在东亚利益上有摩擦后,罗斯福吃准了日本政府和精英的敏感点,用限制移民政策对日本进行“报复”;德日意同盟因人种问题而导致互不信任,必定走向失败……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自己不仅仅从政治史、外交史的视角,而且从社会文化史的语境着手,来研究人种体验这一有关人类情感的课题。
长期以来,人种问题在日本被视为禁忌和避讳之事,对西方的自卑感以及对亚洲其他地方优越感仍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近代日本的光和影现在依然悲哀地化为’肤色’的忧郁,持续地存在于日本的心性当中”。正如作者所言,“近代的西化、战后的国际化,乃至当代的全球化归根结底都未逃脱西方,只不过是以‘世界’为名目,积极接受西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