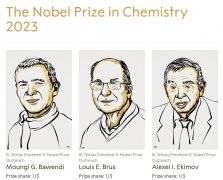天辰app在大理偏远的白族村庄,如何建一个非典
已有人阅读此文 - -
立夏那天,下午日食发生时,我正在沙溪古镇上,跟随一位本地工匠参观一座维修中的建筑遗产,有百年历史的马店欧阳大院。沙溪是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欧阳大院始建于1912年,1917年完工,这次大规模的修缮始于去年夏天。工地上的工匠以一扇雕花木门为例,向我解释修复中新旧部件的联结关系时,光线忽然就暗了下来,一种稠密、有重量的昏暗,让这座古老的房屋随之笼罩在一阵神祕的木香中。
芬兰建筑师尤哈尼·帕拉斯玛在《肌肤之目》中写道:“现代主义设计普遍庇护了我们的思维及眼睛,但它让我们的身体、感官,乃至记忆、想象与梦想变得无家可归。”而在这栋传统建筑昏暗的阁楼上经历的日食时刻,让人的感知与一个建筑的生命,乃至身心内外更大的范围,紧密地联结,并呼应起来。
建筑改变了人的视角
当日去沙溪的缘由,是探访南京先锋书店的第五个乡村书店——先锋沙溪白族书局。
在欧阳大院,不期然地沿着“建筑的功能与材质”这个话题,工匠提到了先锋沙溪白族书局。书店位于沙溪镇镇中心北面的北龙村,步行过去需要20分钟左右。
工匠师傅说,沙溪的先锋书店原来是一个村民集体使用的粮食加工作坊,因为不是民宅,建筑材料并不讲究,很多材料是当年东拼西凑起来的,比如屋梁,从原来山上的一座庙里拆下来,重复利用,“过去农村建房,总要尽力为之地重复使用材料”。今天的环保主义者倡导的“零废弃”,在乡村社会,早已是建筑传统的一部分,而让这位负责古建维修的老工匠赞叹不已的是,从原本鸡飞狗跳的粮食加工作坊到今天的书店,时空转换中反映的是建筑功能的巧妙转化。
沿着村民指的路往北走,按图索骥“那座山崖正对着的村子”,经过河岸、长满烤烟和玉米的田野、一所乡村小学,到了北龙村,但找到先锋沙溪白族书局,还要费一番周折。小巷的尽头,几乎到了村子边缘,靠近坡地的空地上,先锋书店的主体建筑在一丛苍郁的翠竹边显露出来。洗练、考究,又不失松散的意味,建筑本身给人的第一印象,打消了沿路一直困惑我的问题——为什么会在这里开书店?
先锋沙溪白族书局是建筑师黄印武主持设计、施工的第一个书店建筑。黄印武与沙溪结缘,是在世纪之初。当时的沙溪古镇,以其完备的建筑遗存和传统村落相互关联的形态,进入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学者的研究视野。2003年,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和剑川县政府共同组成了“沙溪复兴工程项目组”,天辰app黄印武负责主持古镇寺登街的建筑遗存修复工作。
2010年,修复工程到了尾声,黄印武意识到“在沙溪做的事情,似乎还没完。不知道修复之后的建筑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和发展周边的乡村”。在他的观念中,乡村建筑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建筑本质上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建筑也可以改变人的视角”。
沙溪坝子(云南人对山间平地的称谓)乡村建设的整体规划,始于2015年,当时确立的基本框架是,通过寺登街来带动周边村落的发展。目前,纳入首期规划的6个行政村,皆环绕寺登街,其中包括先锋沙溪白族书局所在的北龙村,连接这6个村的环线公路于2017年修好。据黄印武介绍,这6个村有的空心化严重,但北龙基本住的都是本地人,空房很少,建筑样貌与村民的生活方式基本延续了白族村落的传统,这里有一所“江东小学”。
2016年,南京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到沙溪为乡村书店选址时,当地政府给了他几个选项,其中包括沙溪镇最繁华的寺登街广场周边的建筑,但钱小华有意避开喧嚣,“他可能想在更真实的乡村场景中来做书店”,黄印武推想。
寺登街周边现有两个小书店,囍书书店和刺猬书店,一个经营二手书,天辰app一个选书以文史哲和艺术类为侧重。两个小书店分别占据小小一角,生意清淡,更像是长住沙溪的人的一个社交空间,或者旅客偶然的歇脚处。经营囍书书店的老莫说,书店建设的主体是读者,书店仅提供读者所需,不愿因书店运营而刻意引导读者,更希望书店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两个书店的经营者向我透露,5月南京先锋书店的员工来沙溪团建时,四五十位员工拉动了小书店的销售,是他们开店以来营业额“激增”的几天。囍书书店的店长跟我谈到一个细节:钱小华借走一本关于“有机书店”的非售书籍《把书店开进偏乡》,“第二天便还回来了”。
开刺猬书店的于迪说,在沙溪开书店一年来,见到的真正看书的人实在太少太少了,一个月一单生意都没有的情况也是有的,不用说生意,就是来借书的也很少,“一年来,真的感觉到人们对书店有了兴趣,甚至买书的人变多,其实还是在有了‘先锋’之后。一个这样体量的成熟书店,才能在沙溪有如此的影响力。”
隐没于村舍的书店,对村民来说,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建筑
做乡村书店建筑的设计,黄印武很自然地会想到两个联结点,一个是传统村落的风貌与乡村社会的整体性,一个是与先锋书店品质相匹配的建筑作品。
2017年冬天,先锋沙溪白族书局改造工程刚动工时,我曾跟随黄印武到过工地现场,当时最强烈的印象是,一道荒凉的山坡下的一个过于破败的建筑,一个由飘满尘灰的屋架和鸡飞狗跳的地面组成的现场。
刚开始,黄印武没有奢侈到花很多时间到现场,观察不同的季节、时间光线的变化和状态,但会经常来这里。他说:“我是在场地中做设计的人。建筑设计,核心的问题在于把空间的界面,以及空间所要容纳的内容:材料、光线、行为活动(与布局相关)——这些单个的元素合理地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建筑,这就是一个建筑应该有的样子。”
书店的前身,一个粮食加工作坊,本身就在乡村,因而和乡村的关系更容易建立,建筑的样式、所使用的材料和乡村的联系是其固有的,而这样一个建筑的改造,更重要的部分是做到现代人的认同,书店有一个更大的客户群,需要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时代标准。
与寺登街建筑群保护项目不同,这个老房子,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保护项目,它更多涉及利用,因而黄印武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加入新的建筑元素和信息,与旧的建筑重新组合,但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个系统的重构。黄印武说:“修复寺登街的时候更多是去读懂遗产背后的信息,所以叫‘阅读时间’,在这里做得更多是‘与时间对话’,用新的东西来满足现代的生活需求和回应既有的建成空间。”
由废弃烤烟房改造而来的诗歌塔 摄影/王馨
由废弃烤烟房改造而来的诗歌塔 摄影/王馨
完成之后的书店建筑,由三个大的区域构成:经过修缮的粮食加工作坊作为书区,是书店的主体部分,穿过一个空廓的室外场地,与书区相对的地方,地面被抬高了,新建了咖啡馆,咖啡和书区之间起伏的坡形,构成了新的观看关系,由高向低的俯瞰视角,让书区主体建筑的屋顶更大面积地显露出来,使得建筑整体更轩敞、通透,一改过去老房子低矮、闭塞的感觉。穿过咖啡馆,右侧是一幢废弃的烤烟房——窄而高的塔形建筑。改造保留了烤烟房的基本构造,但加高了建筑,建筑内部狭窄中空的部分,悬置了以钢索牵拉压制层板的旋转楼梯,既是路径又像是一件装置作品,钢索和层板的细密线条随光线明暗变化流转,让这个整体静寂而质朴的建筑,多了几分游走的趣味。
黄印武尊重乡土建筑技艺与材料,也愿意使用板材等实用而低调的材料 摄影/王馨
黄印武尊重乡土建筑技艺与材料,也愿意使用板材等实用而低调的材料 摄影/王馨
几乎是受一种本能的驱动,从一开始改造方案成形到施工完成,没有太大的调整,最终呈现的建筑形态,是场地空廓、松散,与建筑细节的精致感,建筑师对序列、尺度与比例的精确控制相对照,留白与所欲呈现之物相呼应。
书店的主体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通透的屋顶和南部一整面玻璃窗,玻璃窗把屋外苍郁高大的竹子引入建筑内部,在一个静态空间中汇入动势,让氛围既澄净又灵动。
粗陋的现代建筑,对于乡村有可能是灾难
第一财经:今天的建筑技术几乎可以让设计师发挥所有奇思妙想,建筑的人文性是不是更容易被忽略,建筑师的人文素养应该发挥怎样的影响?
黄印武:有人问我,这个建筑该怎么拍?从哪个角度拍?我想我并不关注如何来“印刷”一个建筑,建筑应当回归使用和体验。
建筑师如果不考虑建筑为什么而建,为什么人而建,如果没有人文素质,就是一个工匠,建筑师不同于工匠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受过系统的训练,你知道建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背后有人文的精神,而不是仅仅知道如何把一个房子建起来。这个问题说起来有点绕,你认为建筑能解决某一个社会问题吗?恐怕不能。但是你认为建筑可能改变世界吗?有可能。为什么说体验很重要,这可以改变人的视角。你营造什么样的空间和氛围,真真切切地影响每个人,也有可能去改变每个人,所以建筑的语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
第一财经:你认不认同在乡村建很现代的房子?
黄印武:从我的观念来讲,在一个传统村落里建一个很现代的建筑是没有问题的,但会给现实管理带来很大麻烦,因为你不能保证所有人在建现代建筑的时候,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品质,而只有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在传统村落里做现代建筑才能成立,就好像卢浮宫的广场里也可以有玻璃金字塔。当传统的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品质很好的现代建筑的时候,很容易被其他村民模仿,而本地的工匠体系和技术能力,往往造成大量东施效颦的赝品,这就有可能是灾难。其实新旧有很多种交融、对话的方式,我选择仍然做传统的风格,其实是有意为之。
第一财经:白族传统建筑比较依赖本地的工匠,你这一次与他们合作有什么感受?
黄印武:我一直都是尽量用本地的匠人和本地的材料。先锋沙溪白族书局最开始我是想请本村的工匠做,但现实很无奈、很尴尬,最后还是用了以前合作过的工匠。一方面涉及工匠体系,传统工匠是基于经验的建造,而我的设计实际上是基于技术逻辑的,工匠不能系统地理解这种设计,这就造成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工匠精神正在消失,建造的品质难以控制,即使按传统做法也达不到传统的效果。所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